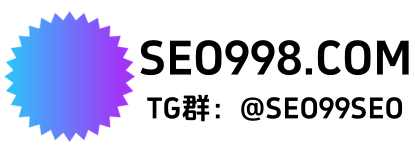Zaker健康:91香蕉国产电影-陆兴华:城市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

1- 什么是城市?
城市是我自己每天谱写的一个曲子,用了“主题与变奏”这一格式,如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那样的结构。我每天写出了一首新城市。
上午陷在办公室、会议和表格中了,中午是在难吃的食堂和昏昏的脑袋中度过,开完会议已下午三点半,我钻进了地铁,车厢里也是压抑的一大片。到了一个当代艺术展览上,触发了与许久不见的好友的一场意犹未尽的谈话。然后就用此时的心致,去渲染了我刚刚过掉的那很不满意的大半天,使我又写出了一首今天的我自己的城市。
2- 弗洛伊德的小汉斯案例
城市空间离间了我们,反过来也架空了我们的家庭、社会关系。弗洛伊德的小汉斯案例告诉我们,由城市的空间隔离带来的微观法西斯,已成为今天的城市压迫的动力源。由于资产阶级的财产界线,小汉斯不被允许与隔壁穷人家女孩玩,只能从窗帘后看外面的现实,只能围着父母的床玩,被妈妈搂抱着来获得亲情。于是,小汉斯就得了神经症,有了施虐幻想,失去了自己的领土后,就要将自己神经症当武器,像小暴君那样,用他自己的症状,去迫害他的父母。
3-城市曾经是献祭、失去之地
人类学家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1928年的“消失的美洲”一文中这样描述城市必需的一场献祭:“在那个威尼斯那样富裕的城市里,阿兹特克人的祭司用手掏出人祭品的心脏,举过头顶,献给太阳。心脏还在那里有机地跳动和喷血。然后,尸体就被重重地甩在地上,并被踢到阶梯的角落。当晚,祭司们就会来吃它们。这之前,它们将被剥皮,剁块和烧煮。结束前,神像、神庙的墙上和鲜花上,全都被蘸满了血。并不动手杀人的祭司们,会用祭品的脸死贴自己的脸,将祭品的身体的皮肤,去贴在自己身上,狂情地向自己的神祷告。这就是来自恐怖的幸福的吃惊”。阿兹特克人必须做如此残酷和恐怖的仪式,才能让城市一次次意外地重新找到幸福。
而今天的城市早不会做如此的献祭和狂欢了,陷于资本积累过程,永远无法自拔,心理和社会问题积压而内爆。城市成为资本的积累空间,如榨汁机或高压锅那般处理着我们的身体的再生产过程。
4-我们都是城市拾荒者,只好捡到什么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了
本雅明把城市看成人的城,认为城市的所有建筑都是前人留下的潜在的神话装置。街道和门槛也是先人对我们施下的魔法阵,如妓女掀起她们的裙边一般,时时来撩拨我们。在城市里,我们与之前的所有时代调着情。
本雅明还说,在巴黎行走,我们是同时行走在罗马、那不勒斯和马赛的街头。走在今天的上海街头,我们是一一路过了不同时代的永安、春天、银泰。实际上,每一条街都是一块辩证之地,鲜活、移动、复杂,既能给我们领路,也能让我们失去方向;既在暗示我们如何去造它,也示范了我们怎样就能拆迁它。
5-城里人是失去了森林的印第安人
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说,城市是蚁穴;栖居地和栖居者之间互相定义。城市也是我们的外骨骼,是我们一路留下的骨壳,死去的前人也都这样留下了他们的骨壳。这就如海底的贝壳层,堆成了我们脚下的这个城市。而每一个城市人都是裹在壳里的一座大酒店。
他们总已在裸奔,但在城外却无法生存,正如白蚁在自己的穴外,就会找不着北。
6- 在城市中成为公园
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 )这样分析黑泽明的电影《活着》:主人公必须死了,因为他做完了他觉得他一生中最想做的事:给市民造了公园,装上了秋千;这之后,他快乐了,可以死了。
在城市里,他成了一个公园。这是我们的城市营生的最高目标。
美国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说,如能再生,我最想成为公园。他还说,我的城市回路才是我真正的性关系;我与我呆过的那些城市的关系,是性关系。
7-理想城市是一座珊瑚礁
在这个理论物理学说的泡泡浴宇宙里,我们就如躺在浴缸里,在无数个对象之间洗着澡。有着泡泡浴结构的珊瑚礁,或被这样地扁平组装的,才是理想城市。
哲学家莫顿(Timothy Morton)说,伦敦是一个你在里面住上50年也搞不大清的城市,大、小路总是太多。你永远摸不清这一伦敦性的。它暧昧、压抑,但也给你带来许多欢乐。街道、公园、卡车、人群构成了伦敦,但伦敦并不只是它们。伦敦并不是一个比它的部分更大的总体,但伦敦也无法被还原到它的各部分。特拉法加广场上的鸽子表明,伦敦并不是我的心灵的效应,也不只是一个人类构筑。它显然也不是只有我坐Victoria Line地铁到PimlicoUndetground Station去Tate Gallery看展览,或因想念伦敦或写一个关于伦敦的句子时,才存在的。今天的伦敦是对过去的伦敦的一次拍摄。你走过伦敦的街道,就是穿行在它的历史段落里的那些句子之间。
8-强悍的人才搞得定城市
温顺的人已不需要城市,因为他们把城市当成了冰箱和婴儿床。后-历史中的人类也已不需要城市,他们让城市萎缩成一个地下控制中心,只保留适合于被监控和被自动化的那些部分。
也许,流浪汉才是更强悍地使用着城市的呢。
9-上海的源头在哪里?
墓地是城市的起源。城市开始于最早的先人的墓地旁边,被拖着、拉着地来到了今天的全行星计算平台之上。
城市哲学家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说,村庄里的洞、石、古树、清泉、人工物,墓和由它们构成的绝对空间或神圣空间,是城市的源头。
所以,静安寺是上海的源头。它一开始是村里的寺,后来被借作这个城市的神圣空间。本地的有钱人也的确是一直这样地对待静安寺的。所以,是从一个村里的庙中孵养出了上海。
10-城市是我们扔垃圾时得到的一个副产品
扔和捡是城市活动的本质。是我们将喝完咖啡的纸杯扔进垃圾筒这样一个下意识动作,才一不小心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城市。无论派对还是游行,留下的总只有外卖盒。如果认真关注它们,你就马上成了城市考古学家,而且会发现,出土罗马远不如出土当代城市更有意义:看懂当代城市的垃圾,你就用不着去考古罗马了。所以,城市从来都不新。
所有时代的城市都是共时地存在的,如果你有考古学家的眼光的话。
而且,城市是不会被我们“失去”的。各个版本的老广州就在当前的这个新广州的人们的脚下,因为我们还将接着扔各种纸杯。
11-过去的城市的所有版本争相在今天的青少年的涂鸦中露脸
根据哲学家哈曼(Graham Harman)的以对象为导向的本地论,所有时代的开罗都同时存在于街上和广场上的青少年涂鸦之中,都抢着要来当代亮相。
12- 城市是由我买不起的东西构成的
在城市中,买不起的东西才能更诱人地给我陈列在那里,引诱着我去替代性地占有它们,用了图像,用了塑料或塑料袋,去过干瘾。四合院、苹果手机店和三里亭的神秘夜店,才构成了一个能够唬得住我的北京。
但是,每一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去居有一种自己的城市风格或时尚,哪怕不能在时尚和艺术上领导潮流,至少也能在个人穿着、装饰和家用物品、美食和发型上,去独树一帜。
13-我住过的那些城市……
必须用幸存者的眼光来看我住过的那些城市和周边的小树林。艺术地去看城市,反而是不好的。必须记得:我住过的所有城市都已经是我的奥斯维辛。回访它们?不可能的。
今天,我是又一次不得不在我不得不呆着的城市里幸存了下来。
14-城市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
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说,我们必须继续“写”出我们自己的城市,也就是主动用更新的技术,去作出集体的城市体外化。但是,对城市的这种新的写,又反过来会对我们有毒。但作为一条集体体外化的大船的城市,在生物圈中仍将是我们的集体深度学习的系列成果。城市将是我们的学习的领土。
15-城市哲学系列
这是本人的一个长期写作计划。目前出 版的有两卷:《走向全球城市社会:城市哲学2》(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人类世与平台城市:城市哲学1》(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第3卷《城市的收入和工作》和第4卷《学习的领土》将在之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