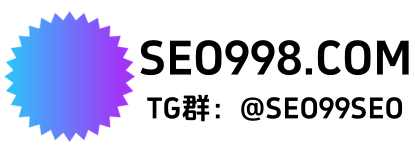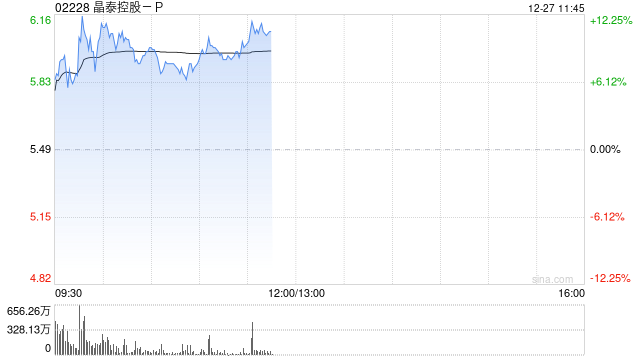网易游戏手机端:精品福利视频网站-读书小组|王安忆《儿女风云录》:人,在历史的缝隙中
编者按:《儿女风云录》是王安忆最新长篇小说。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上海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王玮旭主持的“此刻·上海大学当代文学读书小组”,目前有14名中文系研究生、本科生成员,他们在近日就《儿女风云录》进行了集中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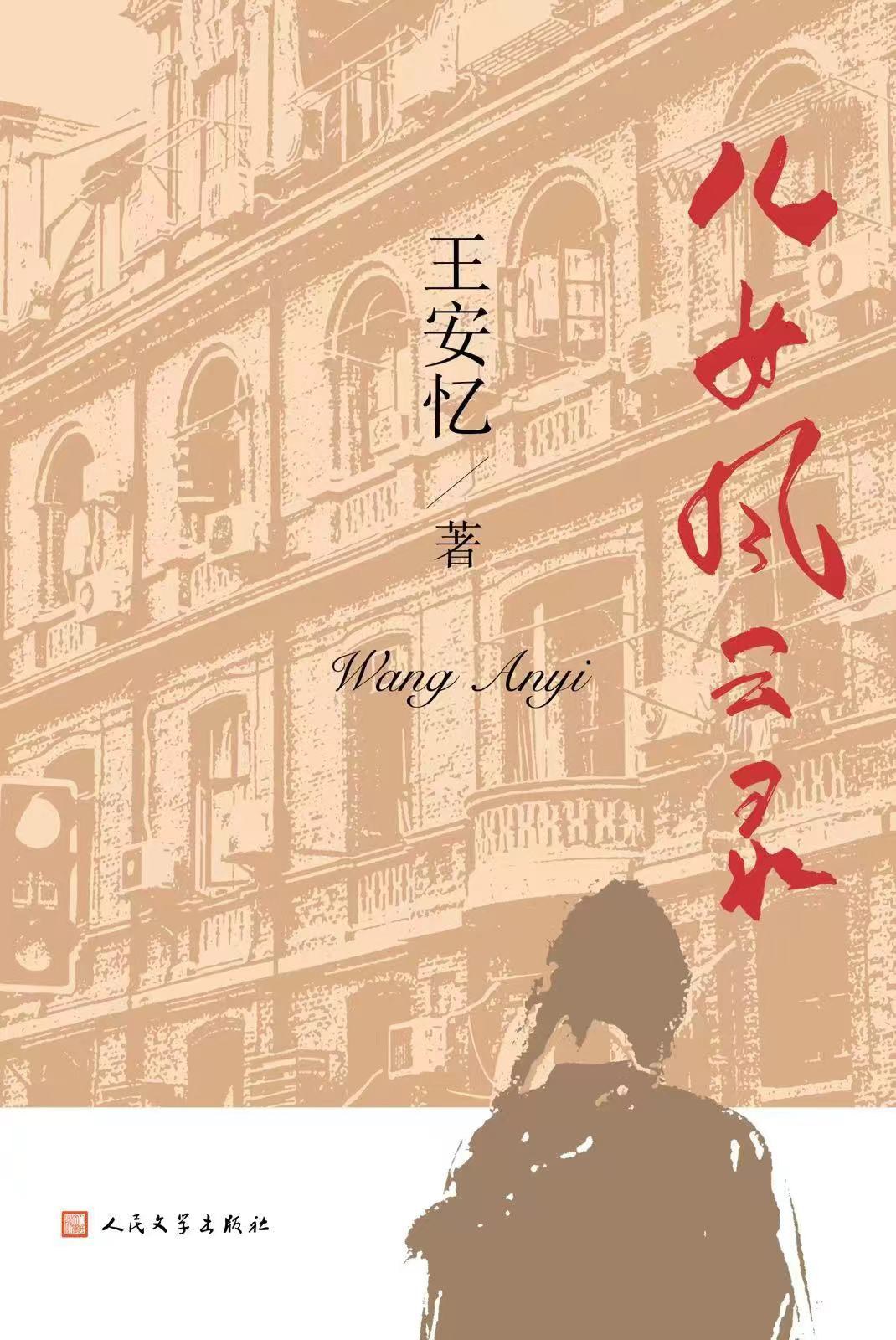
王安忆《儿女风云录》,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儿女”与“风云”
刘依涵:小说标题很容易让人想象一个气势磅礴的群像故事,不过小说主人公小瑟周围的人物,上一辈的父母、后辈阿陆头都没有占据太多笔墨,小瑟的家庭史远没有《天香》中那么庞大和详细。“风云”所带有的动荡感,也多少被王安忆对于日常性内容的书写掩盖了。如何理解小说的“儿女”和“风云”?
任星潼:小说开篇有一段关于舞厅外的夜市和菜场的描写,其中有人物的动作、嘈杂的声响、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各样气味等等,最后段尾将以上这些略总结为“这里有一种绿林气,来的都是好汉”。这一段尝试建构起“市井”与“绿林”、“普通人”与“好汉”之间的对接关系,借用绿林好汉原本的江湖气打开书写都市生活的一种新的可能。或许这才是“风云”的所指。
崔嘉慧:虽然讲述了社会风云变幻之下的人物境遇,但社会历史不是小说所希望传达的“内容”或潜在主题。小瑟一家人与社会历史是脱节的,在主观上他们对历史趋势和社会事件不感兴趣,而是依靠阿郭去了解社会与时代的变迁,阿郭是小瑟一家人得以与宏大历史产生关联的“中介物”,同样,他们也依靠阿郭才能在宏大历史中生存下来。就此而言,阿郭才是符合“儿女风云录”这个主题的字面意义的人物,阿郭完全具备游走于社会变幻之中、为自己谋划前途的行为能力。
阿郭这个角色本身也值得商讨。阿郭具有敏锐的历史嗅觉,但是却对“大历史”不感兴趣。文中多次写到阿郭对革命历史兴趣了了,他听故事时喜欢听家史而非社会历史。这些都意味着,阿郭是一个消极“介入”历史的人,他对历史的把握和游走只是为了自我和小瑟一家人谋划,毋宁说其他人物比起阿郭而言对时代变幻是更加消极的。就此而言,《儿女风云录》通过小瑟呈现出了“反典型”的风云儿女。
在结尾阿陆头和阿郭的对话中,小瑟的“反典型”特质凸显了出来。在阿陆头看来,小瑟和她是两种人。这一划分方式是依据两人所处的不同阶级,显然有些粗浅。而阿郭的划分方式是将人分为新人和旧人,判断的依据是是否跟上了时代的潮流,是否读懂了并操持着社会的语法。而小瑟特殊之处在于,他不是完全的旧人,但也不是新人。由此看来,阿郭和阿陆头的两种判断标准都无法完全概括小瑟,他在两种标准中都是无法被除尽的“余数”。
叙述者称小瑟是“历史的秘辛”,这一定义所蕴含的深意或许是:他还不够成为历史的真相,但或许历史得以发生、推演的某种“机密”就在这个未“开蒙”的、游离于时代历史的人物身上。就此而言,他也是一种“风云儿女”。
与历史“擦肩而过”
任星潼:1980年代以来,文学的历史书写呈现出建构个人史的倾向,对此我们或许都可以追问,个人史的表现限度在哪里?《儿女风云录》当中多次触碰到“历史大事件”,我们发现个人和历史常常出现错位,历史当中的“断点”与个人史当中的“断点”并不可能完全重合。
王佳颖: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大事都明里暗里写到了,但人物似乎总是与历史“擦肩而过”。因为这半个世纪对于国家和国民来说是充满机会的,但又并非每一个人都有资本去把握机会。小说中一段“扳着手指头数数,1979 三中全会;1992 邓小平南方视察;直到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的 2003,就算搭上每一班船,二十年算一代,头尾撑足一代挂零,成为贵族要几代?”对于作品中所提到的作为“中流砥柱”的“小布尔乔亚”而言,他们没有办法“搭上每一班船”,即使碰巧走上历史的传送带也只是一种擦肩而过的关系,比如小瑟进入文工团,埃塞俄比亚和啧啧抓住商机,他们只能蹭上历史快车的边缘,他们不是所谓的成功者,在转型期他们处在将离未离的中间状态。但恰恰是这些人构成了历史的大多数,尤其是这半个世纪的上海的风云中的大多数。
王玮旭:佳颖提醒了我们小说可能存在一个明显的主题——小说主人公姓“卢”,外号是一个字“瑟”——这很像是作者刻意暗示我们,小说所写的是一个失败者(卢瑟)的故事,一个人在不断前进的时代中走向失败的故事。这一失败有其个人因素,也有时代的原因,存在着偶然与必然。这是值得我们去厘清的问题。
张佳雯:我关注到小说中人对于历史的回避。阿陆头的男朋友被传出是“缅共”,在阿郭向大家解释这一内容时,原文写到,“全称缅甸共产党,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社会主义联盟成员。在座的人像被施法,定住了。稔熟的阿郭也变陌生了,他是谁,从哪里来?”“上海市井里的政治,总是隔壁的隔壁,邻居的邻居,这样,阿陆头的传奇又变回到日常生活,大家都松下一口气,危险解除了。”这就写出了在全新的环境中,宏大修辞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张感。当阿郭想要在市井生活间操持这套话语的时候,他面临着被驱逐出人群的尴尬。小说其实并不回避对于所谓的宏大修辞、革命词汇的使用,诸如“阶级”“世界革命”“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等等都会出现在人物的交流中,但脱离其诞生时所依赖的宣传机制,这些词汇不再具有串联起个人与集体,在历史中赋予个人意义的功能。在宏大修辞失效的情况下,使个人与历史再契合的叙事是否还有可能?
张烨:王安忆用一种密集的语言置换了单调、重复性极高的革命话语,这种效果已经不同于王朔以来以戏谑调侃的方式对于革命话语的消解,但是又称不上崇高。相反,叙述者的腔调极为平静,历史擦身而过但波澜不惊的感觉,而且对于历史有自己的评判。这背后是对时代话语的“釜底抽薪”?用这样一种腔调去叙述一个横跨半个世纪的故事,是否能够注入更丰富的历史内涵?
“膜”内的人
姚文嘉:小瑟的一生都是疏离、无归属的,在体制外漂泊,始终被一种流浪的危机笼罩着:“他向来不是有心智的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寂寞,其实是金粉世界的局外人。”如作者所写,小瑟和世界之间有一层膜存在。这膜束缚着小瑟,但也同时保护着他。
施松辰:全文有一组词反复出现,即“形而上”和“唯物/现实”。旧上海的屋顶之间显露的天空是“形而上”的,那时小瑟对白俄校长、校长夫人和交际舞会沙龙组成的环境没有疏离感;在“文革”下放期间,小瑟对朴实且有些野性的小二黑及其家庭也是没有疏离感的,他感受到真实的露水、星空和爱情,这些东西对小瑟也属于“形而上”。这里就插入了小瑟跟小二黑家老太太对“形而上”和“唯物/现实”的讨论,他们基本上认为“现实”就等同于苟且,而小瑟想到“电影是上海这个唯物城市的形而上之物”。所以,这组词就象征了小瑟精神生命和人生中价值的两极。但在结尾处,小瑟差不多要下狱时的一段独白,他却声称自己“从没有过形而上的想法,他的一生都是浮泛过去了”,很明显跟他之前的表述相悖,这是作者有意制造的文本内部的矛盾。
我们若由此反观小瑟的种种“疏离”,会发现这种疏离的本质是一种割裂。譬如:作为社交游戏的交际舞会被阴差阳错地改造成革命宣传舞,又在时代翻覆之后变成一种供给市民消遣的谋生手段,每一步都是目的与实存的偏离,小瑟一直在被迫重新决断他的生活,从而丧失了长远的谋划和连贯性。当自由抉择越来越削弱,而被外界摆弄的宿命感愈发强烈时,人就会变得苟且而丧失面对时代的主动性。
崔嘉慧:在情感关系上小瑟是晚熟的懵懂状态,在行动上表现为逃避,每当有问题时小瑟的解决措施便是逃避,这也反向使他不断错过成长的契机,因而总是处于失势的位置。面对时代的风云变幻,小瑟仍然是“未开蒙”的姿态,他对历史事件毫无招架之力,完全无法也不想去把握社会和历史的进展。
如果将爱欲与社会化的双重晚熟在小说中视为一体,那么小瑟对时代的态度就变得饶有意味。他在情爱关系上的被动并不完全是被迫的选择,甚至某些时刻他也乐在其中。他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如此无力,也不只是因为“历史变革掠夺了卑微个体对命运的掌控能力与权利,使个体只能在时代变革下随波逐流”,这种判断将个体置于一种纯洁无辜的被害者位置。事实上,这个个体的失势,某种程度上还是自我选择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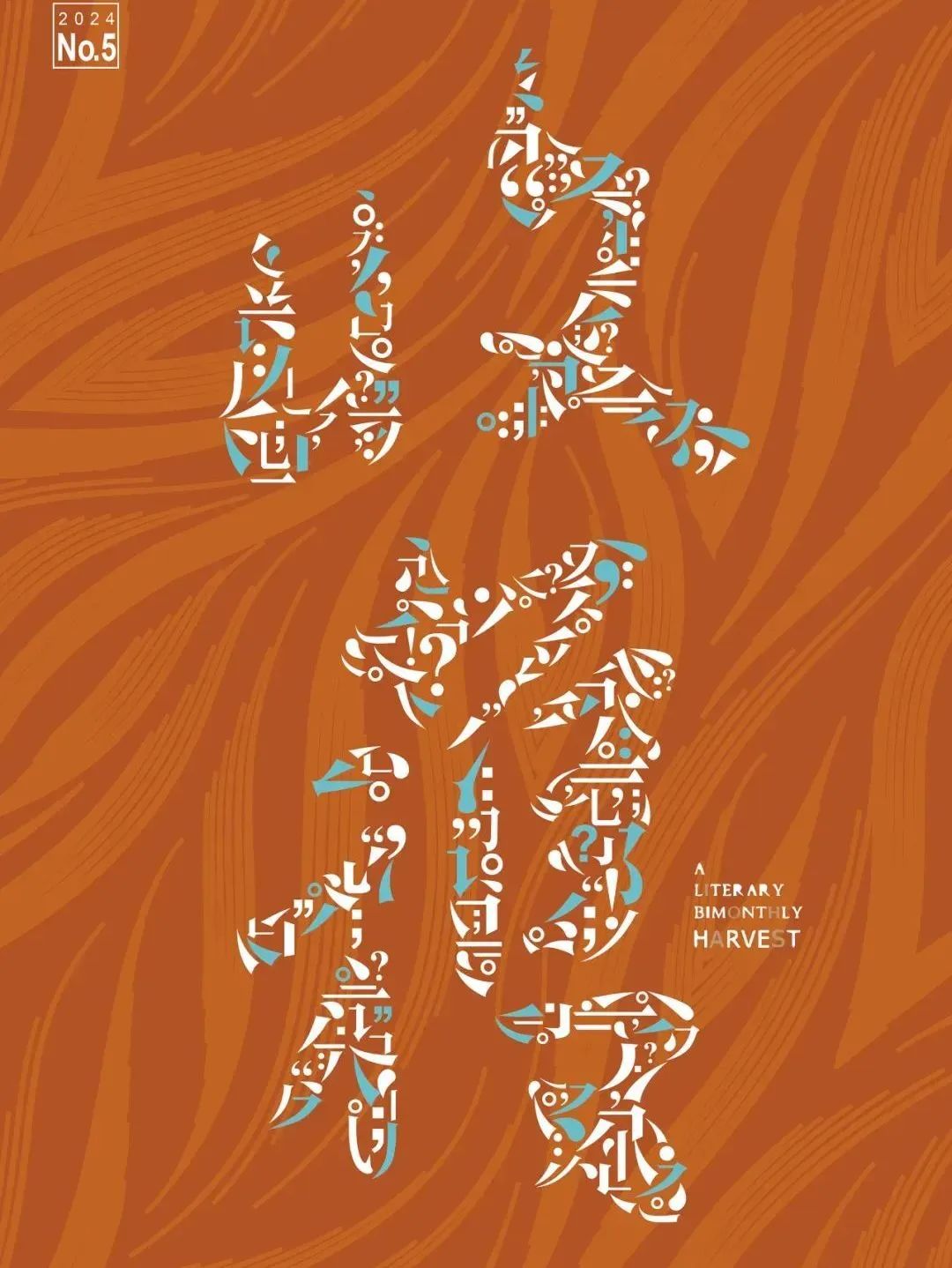
《儿女风云录》首发于2024-5《收获》
风云里的上海
刘依涵:《儿女风云录》里出现的地点其实并没有局限于上海一个城市,小瑟的人生中有好几次离开上海的经历,比如去北京学舞,比如工作后频繁出差,后来甚至移民到美国,所以小说的空间范围其实是比较广的。但小瑟每一次离开,最后都回到上海,因此我还是想讨论一下《儿女风云录》中人物与上海的关系。
以小瑟年少去北京学舞为例,首先小瑟这个人物肯定没有他母亲那种“上海之外都是乡下”的骄傲,但他去北京后萌发了一种“身份区分”的意识,他将舞蹈老师和大嬢嬢归于到同类的“官派”,他身上的上海印记通过朴素的感知体现出来。等到他回归上海时,他才会有意想起北京,“此刻领略到历史的高古的魅力”,也就是说,小瑟这个懵懂的人物唯有在离开并回到上海这个空间位置,对外界事物产生一种超出他日常生活的认知冲动才能够出现。
另外,虽然《儿女风云录》里的上海没有《长恨歌》里那样带有传奇色彩,但结尾老法师被捕前有一段描写,“就在这时,他看见江面,金红色的水平线,飞着许多墨点子,是江鸥。”以及后面紧接着的俯瞰视角和《长恨歌》开头鸽子俯瞰上海弄堂不无相似,如果说小瑟的数次离开是一种人看上海的视点,这一视点最后则转变为上海看人,那么,《儿女风云录》中的上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施松辰:小说中的“上海西区”很可能就是曹家渡,因为老上海人有俗语“东到杨树浦,西到曹家渡,南到高昌庙,北到火车站”,加上那一片地方正好是二战时期的犹太人自治区,跟主人公的族裔也相符合。小瑟的家庭故事基本上发生在一个三层排楼的建筑结构中,这是典型的上海市区石库门建筑景观,而非最繁华地区的花园洋房,所以应当地处市区外围,也符合曹家渡的位置。而且苏北人聚居的虹镇老街也在那一带,跟小瑟的家庭背景也符合。所以,小说写的是有别于经典上海中心市区的外围市民生活。
陈榆菲:就“上海性”而言,小瑟记忆中的弄堂从大家族慢慢拆散,但是“亲缘出去,一户户陌路进来”,他们一家人坚挺在这里;后来他虽然一个人,也依然坚挺在这里。这样的情节特别像王安忆老师的《本次列车终点》中一直执意回到上海的男主人公;也让我想起阿舍小说《阿娜河畔》中,一直执意要求远在新疆参与劳动的女儿回家的情节。这似乎说出了“上海”的地方性本身,在“变”之中依然“不变”的,在“一切烟消云散”时那依然“坚固”的。正如小说中,小二黑在与小瑟谈论他的血脉时,以玩笑的口吻提及“寻根”一样,上海虽然有着“海纳百川”的城市品格,但内里有非常坚韧的精神。小说这样讲“城市的韧性”:“这城市开埠以来,历经无常命运,财富消长往往一夜之间,麻雀变凤凰或者反过来,所以,就有韧性”。我觉得这可能是近现代以来的风云激荡中,上海这座城市所一直坚持的珍贵的品质。
“晚期风格”的浮现
陈芸静:从宏观的情节设置上看,《儿女风云录》与《长恨歌》有相似之处,存在某种追寻终极意义的写作愿望,通过对过往进行梳理、评判,进而获得阅尽尘世的超然。不过与《长恨歌》不同,这部小说同时还在摆脱某种规约,比如略显突兀的结尾,以及最后阿陆头和阿郭在马路上的停留,似乎预示着有关老法师的一切还在继续。老法师身处的已经不是旧繁华梦的上海,它的内部既有市井的生活日常,也有市场的波云诡谲,甚至还有革命时代的余音。小说字里行间显示出一种沧桑感,虽然词藻句法绚丽,却带着和谐与宁静,常常有某些哲思疏解着情节上的跌宕起伏,似乎暗示着与人生难题的和解。总体来说,我们对于王安忆老师总有一个期待,总是希望她能够进一步自我超越。那么《儿女风云录》是否抵达了某种新的境界?是否形成了某种类似萨义德所说的“晚期风格”?
刘依涵:《儿女风云录》有很多王安忆以前作品的影子:老法师、上海、市民日常这些因素会让人想到《长恨歌》,老法师在父母妻子面前的表现以及对于感情的软弱又让我想起《红豆生南国》中的主人公,学体操的阿陆头与《桃之夭夭》里的郁晓秋有几分相似,另外家族史与社会史的交织又很像《一把刀,千个字》。
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主要内容集中于主人公的个人史,但小说的个人传奇色彩不如《长恨歌》。另一方面,小说不止于个人史,但好像又不像《五湖四海》那样可以较为明确地被归纳为“改革开放创业史”。《儿女风云录》提供了另一种观察历史的方式:从人中去看历史,而不是从历史中看人。
姚文嘉:整体感觉上,《长恨歌》的叙事类似于工笔画般的精细描摹,《儿女风云录》中的笔法则是写意的,精妙处由块状的色彩挥洒、堆叠营造而成,并不靠一笔一画的明晰线条。《长恨歌》的叙事明显更偏个人史,在涉及的人物、空间、时间、社会相上都不如《儿女风云录》的跨度广,后者从阿陆头与小瑟同住的弄堂、从民工与老法师都会光顾的舞厅、从各个阶层的混杂处下笔,真正做到了叙述整个时代,并不由于角色所处阶层的不同就将叙事切片。这透露出小说在个人史叙事和时代史叙事之间保持的微妙平衡。
另一方面,作者的笔力又避免了《儿女风云录》成为彻底的时代纪录片,它还是以追踪男主角小瑟的个人命运为主线。小说从一开始就强调男主角的独特性:“话再说回老法师。按常理,他的形体样貌是有特殊性的,一眼就可辨认。”这区别于《长恨歌》中的女主角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在《儿女风云录》中,作者有意选取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传奇性人物作为主角。但小瑟作为男主角,他虽然受到时代直接影响,命运几度浮沉盛衰,却又始终与时代保持着一定距离。由此,小说既绕开了对历史大事件的直接叙述,保持于对角色个人命运的专注,同时又完整地勾勒出了数十年间上海的风云变迁,避免让过于琐碎的细节消解了宏大的时代背景。